看《坪石先生》:作者电影之通俗
更新时间:2025-08-16 04:03:35
作者电影可以通俗吗?事实上,作者电影的来路,尽是通俗作品。 电影《坪石先生》的剪辑指导萧汝冠老师说:“我们要做当代的白居易。这种通俗并不妨碍这仍然是一部作者电影。”香山诗歌之通俗坚劲,诗史美谈。可见在中国人的文化道统上,作者的伟大性与是否高雅,并非绝对的正相关。事实上但凡艺术领域,无论古今中外,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似乎永远是场无尽的轮回: 魏晋时骈文大盛,初唐时韩愈等人便开展“散文”运动,使文以载道、言之有物的文风回归主流;中唐逸诗写尽,名句唱绝,几乎再无突破余地,白居易与元稹便兴“新乐府运动”,使诗歌回归质朴与一种相对通俗的音乐性。(唐诗早有朴质的传统,杜甫的“三吏三别”,正是毫无修辞,冷静记录的作品)清代古典文化封顶,便又有了汪洪二人所倡的“骈文中兴”之事。通俗与高雅正如同太极,大雅中暗隐大俗,大俗中也潜藏大雅。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太极圆转,无使断绝。 无独有偶,“作者电影”诞生之时也是一样。 如今提到作者电影,影迷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文艺片,是艺术电影。可事实上,特吕弗与戈达尔等手册派影评人所选出的前三位作者导演里,无一例外,都是商业类型片大师: 首当其冲的便是希区柯克,之后是拉乌尔·沃尔什,最后是约翰福特。手册派真正对抗的并非类型叙事,而是部分好莱坞流水线电影的情节刻板与人物陈腐。类型叙事的本质是一种以戏剧性统领现实真实的观众心理学,而并非死板的叙事节拍与一成不变的情节设计。 王家卫、蔡明亮、维伦纽瓦、杨德昌、是枝裕和,这些声名如雷贯耳的“文艺片大师”,其实都是深谙“类型结构”的创作者,所拍电影本质上并未脱离类型叙事。他们都是在类型框架内有选择地重点表现某些段落,从而实现自己的独特视角与强烈个人风格的作者:是枝裕和是更注重人物关系与社群结构;维伦纽瓦是将节奏放慢;王家卫将类型的部分段落略去不表。如作为经典的爱情类型影片《花样年华》,始终在“确认相爱”这一节兜转,以氛围代替性与爱,从而暧昧至极。 所以对于电影来说,作者性与通俗性本就是各自发展的两条线,在电影世界中时而交结,时而间离,而最终目标都是打动人心的好电影。 在《坪石先生》中,通俗性体现在视听语言和叙述的方式上:镜头运动不花哨,固定镜头和轨道拍摄为主,声音从始至终坚持同期录音。节奏上和情绪动态上,则语气放平,不疾不徐地展现人物与情节。 作者性则体现在影片的整体气韵与主题表达上:以空间与美术置景来塑造出文人世界,并在重场戏中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气韵:良宵妙摆影竹,玄夜虔讲骈文。这两处情节极具原创性,既透出主创功力,又举重若轻,不甚着力:摆影竹灵动,给于观众奇袭,行动飘逸,一蹴而就,浑然天成;讲骈文深湛,赋予缄默。幽幽冥冥,鬼神浮没,情境如临,灵魂出窍。两处情节的作者性也完全源于电影技法:影竹是电影造型。上次见到具有如此表现力的电影造型,是2017年琳恩拉姆塞导演《你从未在此》的开场镜头;骈文课是声音的的叙事闪前,2021年影片《小伟》在父亲梦里回乡探母的情节里,也出现过相同思路的表现手法,不过《小伟》依靠的是光影。《坪石先生》用的是声音。 主题上,主创强调保护文脉,传承精神,反对少年脑热的投笔从戎与无谓的流血牺牲。国土社稷,将士奋战可再夺,但精神文脉一旦失联,就再难接续了。欧洲为了重续希腊精神,跨越千年方得再现;犹太人为了重回巴勒斯坦,谨遵教义,踽踽千年流浪。(尽管后已有历史学家证明,现代的犹太人与他们心中的祖先——彼时占领迦南的希伯来人已毫无血缘关系,甚至并非同族。) 《坪石先生》的导演曾坦言:“精神是我面对的第一现实。”这一点在宏观历史层面亦有著述,法国年鉴史观学派认为,对一个族群的影响因素这般排列:最短的是人,然后是政治,长一点的是经济。最久的,就是文化。(终极是自然)。可见人类生存之终极追求究竟为何。而当今之国人,有多少能通读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呢?笔者自愧,一声叹息。 但看完《坪石先生》后,又有信心起来。影片结尾,黄际遇振臂高呼:“社会百废待兴,我们报国日长。”在抗战胜利后如此,今日也是。时间,会给予一个文明答案。 即便当今未来是AI时代。文脉之传承,依然要靠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 所以,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,是早早晚晚的事情。骨血里的文化基因与美学倾向,终会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产生回响,使人明晰自己在精神领域究竟源自哪里,又该去向何方。
免责声明:以上内容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,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上一篇:我对这剧期待不高,甚至觉得不太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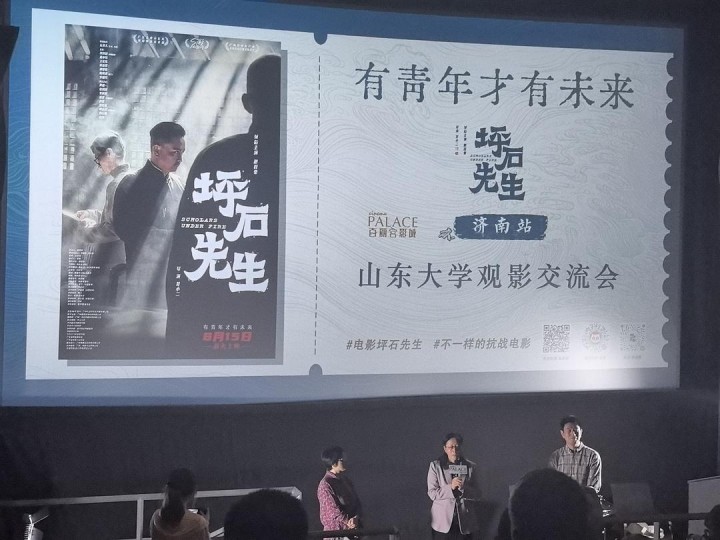 《坪石先生》——读书人的抗战
《坪石先生》——读书人的抗战 共话烽火年代书生的风骨:电影《坪石先生》分享会在省图举行
共话烽火年代书生的风骨:电影《坪石先生》分享会在省图举行 文人登高,痴人命薄:《坪石先生》与《南海十三郎》对比分析
文人登高,痴人命薄:《坪石先生》与《南海十三郎》对比分析 一段跨越80年的岭南传奇!《坪石先生》映后交流引观众落泪
一段跨越80年的岭南传奇!《坪石先生》映后交流引观众落泪